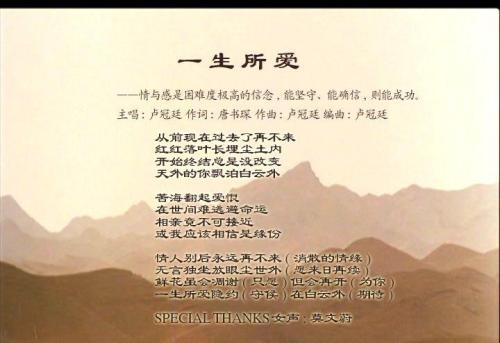昨晚和朋友谈到西班牙,起因是酷玩乐队(Coldplay)的新歌“viva la vida(生命无上)”歌名是西班牙语,而我正好开始做“热情的行方”专题,说到各用三个词描绘印象中的西班牙时,她用的是美女、建筑、劳尔,我的是黄沙(斗牛)、海船和巴塞罗那。
但真正的西班牙绝非表面所见那般浪漫。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地貌是高原和山脉,高耸的比利牛斯山成为西班牙与法国的天然分界线,山高林密;中部的高原地势相当崎岖,而且降水稀少,所谓的“碧血黄沙”也许不仅仅指斗牛场,还概括了这块堪称荒凉的土地上世代的血战;南部是阿拉伯人的故地安达卢斯,在最高峰穆拉森峰的注视下也是一副苍茫悲壮的模样。《房龙地理》里关于欧洲各国的篇章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,西班牙人在历史上注定是要拼尽全力以求得温饱的,因为他们没摊上一个好地方。
然而,这个国家却有几个富庶的意外之地,而且当地的居民甚至不认同自己西班牙人的身份,这些富庶之地是东北临地中海的加泰罗尼亚,比斯开湾畔群山之中的巴斯克,以及曾经是摩尔人(阿拉伯人)家园的安达卢西亚,了解了这些才能够看懂今天的西班牙,在我看来,西班牙是一个强势但拮据的卡斯蒂利亚人(西班牙主体民族)与倔强而富裕的少数民族恩怨情仇纠缠不清的国度,那些恩怨、那些故事、那些不同的文明,实在是扣人心弦。
西班牙最富裕、最发达的地区毫无疑问是加泰罗尼亚。
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区,“加泰罗尼亚”这个词在这里不是一个地区的名字,而是一个民族的象征,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与尊严的寄托,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。严格来说,加泰罗尼亚人应该算是西班牙人的表兄弟,两个民族虽然同属拉丁语系,但加泰罗尼亚语却有着上千年的独立发展历史,它一度是西班牙东部的通用语,不仅仅是加泰罗尼亚地区,它最北覆盖了法国西南部,最南到达巴伦西亚大区,而地中海上的巴里阿里群岛至今也在使用这种语言。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,也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关键,因此在语言的纽带维系下,加泰罗尼亚人始终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着,哪怕面对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高压,这个民族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抗争。西班牙内战中,加泰罗尼亚是抗击法西斯军队的主战场,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亲身参与其中并写下了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一书;在佛朗哥独裁时期,加泰罗尼亚语被取缔,加泰罗尼亚民族组织遭到残酷镇压,甚至加泰罗尼亚的骄傲巴塞罗那俱乐部也遭到佛朗哥打压、诺坎普球场被强制关闭。那是一个不公平的年代,虽然这并不是卡斯蒂利亚与加泰罗尼亚历史上唯一的斗争,但无疑却是最为严重的一次,取缔语言,意味着剥夺一个民族的身份归属,试图将一个民族同化,如果得逞那将对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打击。

但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抗争取得了胜利,佛朗哥死后加泰罗尼亚语重新成为了合法语言,现在已经是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之一了。
历史上加泰罗尼亚曾经是西班牙王国能够建立的重要支柱,但失去了王位继承权之后加泰罗尼亚逐渐沦为西班牙的次要省份,卡斯蒂利亚民族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不同的历史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生存环境使彼此的矛盾越来越激化,但卡斯蒂利亚却没有强势到完全同化加泰罗尼亚的地步,于是在各方面利用王室的力量对加泰罗尼亚进行打压,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作为对峙的双城也代表了两个民族、两种文化的对立(感觉太像重庆与成都的对立了,本是同根生啊…),中央与地方的争斗甚至到了这种地步:巴塞罗那城里有加泰罗尼亚广场,毗邻就是西班牙广场;有加泰罗尼亚大剧院就一定有皇家大剧院;有加泰罗尼亚的象征巴萨俱乐部,那么一定会有与之对立的皇家西班牙人俱乐部。
加泰罗尼亚人相比较西班牙人来说要更开放、更具备冒险精神,也更国际化。如果细心去体会的确会发现他们与主体西班牙人存在很多不同,对于他们对自己民族尊严的捍卫我只能表示钦佩。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也不能对别国内政妄加评价,我只是喜欢这个民族的向心力和自豪感,以及在艰难困苦中抗争的勇气。
或许是因为川渝之间的对立情绪让我比较倾向于加泰罗尼亚吧,虽然性质上完全不一样,但也许我们重庆人更能理解加泰罗尼亚人长期以来的委屈和倔强,以及那种自豪感…
向加泰罗尼亚致敬!